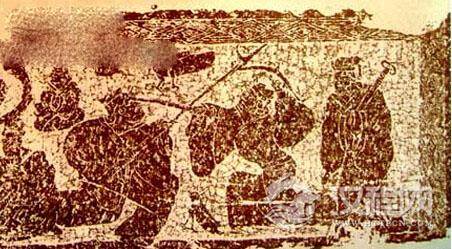功夫神话西渐之累
功夫片再度兴起,凭借着混血的技术、国际化的背景在香港和海外取得辉煌的成绩,或许正表现了“功夫神话”作为“想象中国”的方法之一所具有的独特政治和文化位置。
一
记得80年代初刚一播出香港电视连续剧《霍元甲》时,大街上立即就有无数青少年哑着嗓子用令人费解的粤语发音哼唱:“昏睡百年,国人渐已醒……”在人们心目中,霍元甲一夜之间成了民族英雄,功夫也几乎被目为强国之所必需。后来我念中文系研究生,在故纸堆里翻看《新青年》杂志,发现其第一卷第五期中赫然刊登着以太史公笔法写就的《大力士霍元甲传》,描述霍元甲挑战俄国和英国大力士们,志在一雪“东亚病夫”之耻。这才知道,霍元甲的传奇以及功夫的神话性,原来几十年前就已在新文化运动中埋下了伏笔。
霍元甲在上海创办精武学校,想要用武术来救国。他后来死于1910年,据说是日本人下的毒,随之有关霍元甲的叙述——从《新青年》上的文章一直到去年李连杰主演的功夫巨片《霍元甲》——始终不脱民族主义的政治色彩,遂将他的死与民族的遭遇、他的武功与中国的复兴紧紧联系起来。
事实上,多灾多难的中国在鸦片战争之后一直是“神话”高度发达的时空场域,而功夫是种种令人神往的“神话”中最流行的品种之一。在此需要解释的是,我称功夫为“神话”,不是想要抹煞功夫的现实性,我打心底里还是很佩服那些身怀绝技的武林高手的,同时也知道真功夫正不知要花多少“功夫”来磨练。我所说的“神话”,套用法国哲学家罗兰·巴特的概念,指的是我们关于功夫的话语表述方式。所谓“功夫神话”是以功夫为核心意象的一套使我们倾向于将幻觉当作真实的话语系统,它出现在许多的文学和影视作品、文化和思想议论之中,启发着我们发挥无尽的想象力,去扩张功夫在强身健体、磨炼意志、塑造新民、驱除外敌、救国救民、扬我国威等功能方面的重大意义。
这种想象模式被无数次地重写,塑造出有关功夫的一系列特定表述规范以及语境——比如提起功夫电影,我们不免立即就想到这样一些经典镜头或形象:李小龙在《精武门》飞起一脚踢破上海租界公园门口写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告示;李连杰在《黄飞鸿》中以一身漂亮拳脚打败英美侵略者;而成龙在90年代以来的一系列海外华人题材影片中(从《红番区》到《龙旋风》)不断重塑着同一个类型化的人物形象——那个其貌不扬、受人欺负(或者轻视)的中国人其实是个功夫高手,他总能临危不惧、化险为夷,取得最终的胜利。
这些令人看了感到血脉贲张的经典时刻,都说明了功夫作为某种想象或实有的“国粹”,在有关现代中国的叙述中,承担着使国人从精神到肉体都摆脱绝境的作用。但走笔至此,我的脑海里突然逼入一个似乎有些不妥当的念头——这种种影视形象中的“功夫”,或许都背负着庚子年那些义和拳高手们的尸身,最终的决斗总得是一场与外国人(或者代表外来精神的人物)殊死较量的惨烈表演。虽然义和拳运动的惨烈收场,让大家都知道了功夫敌不过枪子,但民国之后有关这场事件的记忆和叙述,很大程度上参与塑造出了一种“无所畏惧、前赴后继”乃至于“精神胜利”的伦理想象。
二
我倾向于把“功夫片”与“武侠片”区分为两种不同的类型片。“武侠片”有更古老、稳定的传统可以依托,来自中国古代文学想象的侠义精神是它的灵魂,而60年代之后在胡金铨、张彻等港台武侠片大师的作品中,形成了这种电影类型特定的美学形式、道德内蕴和政治想象:基本上采用古装,善用充满寓意的景物,以善恶正邪之争为主要情节推动力,最上乘的武功只是为了发展内力、健全人格,以内心和平为最高境界,并凭此来以一己之力对抗一个腐败堕落的世界。
相比之下,李小龙开创的“功夫片”类型,就很少有胡金铨武侠片的从容洒脱,它的语境中往往离不开民族的屈辱。功夫片的核心形象是霍元甲、黄飞鸿这一系列以功夫来战胜外族入侵者的近代传奇人物,凌驾于一切情节之上的是功夫的无比威力,而在外来强权的巨大压力之下,功夫升华为中华文化的精粹,民族复兴的指望。在这个意义上,李小龙开创的功夫片虽然极尽娱乐之能事,却也常能算得上是“感时忧国”之作。
我心目中最经典的功夫片依然是李小龙的《精武门》。这部电影的巨大成功对功夫片在70年代的复兴起了关键作用,而且也正是这部电影使“功夫”进入英语,在西方变得家喻户晓。影片讲述霍元甲死后,李小龙扮演的陈真为师父报仇雪恨,轮番大战日本武士。
虽然我没做过对于“功夫”的词源学考证,但可以相信的是,随着英语KungFu这个词汇在70年代初期流行起来,反过来也促成了“功夫”在中文中的固定意义——那些总是能找回到李小龙那里去的特定意义。但只要稍加考察,我们就会发现,李小龙的功夫片不仅在题材上把中国放置在国际背景之中,而且在其范畴层面上也是有着混血性的。只是功夫的混血性,往往在神话的浓妆重彩中被掩藏起来,而作为神话的功夫当然总是意欲强调它作为国粹的纯洁性。
在课堂上讲《精武门》时,我总会让学生们大吃一惊的地方,是我告诉他们李小龙的功夫其实不是“正宗”中国产品,而是杂糅了包括西洋拳击、恰恰舞步在内的许多异域元素。作为中国“功夫神话”最核心内容之一的李小龙的功夫,是他在海外生活的结果,这样说不仅是在吸收外来技巧的意义上,而且还与李小龙在异域的身份认同有关。出生于旧金山唐人街的李小龙,在个人经验中重新体验到创造功夫神话的必要性,而他以半个世纪之前中国的惨烈遭遇印证了自己面对强大的西方文化压力、艰辛塑造自我的历程。另一方面,从历史的角度来说,功夫片在作为殖民地的香港发生、发达的过程,也恰恰体现出了与近代中国充满挫折的“国际经验”异常相似的语境意义。
功夫片再度兴起,凭借着混血的技术、国际化的背景在香港和海外取得辉煌的成绩,或许正表现了“功夫神话”作为“想象中国”的方法之一所具有的独特政治和文化位置。而《精武门》把现代中国的“功夫神话”带到了国外,也为东方主义式的中国表述确立了一个新的指示符号。甚至李小龙也几乎成了中国人的代名词——我曾记得有一年在纽约时代广场曾遇到一个黑人对着我拼命狂吼:Bruce Lee!
与此同时,《精武门》的影像记忆在好莱坞电影中一直挥之不去,直到前几年昆汀·塔伦天奴拍摄那部异常血腥的《杀死比尔》,其中不难发现乌玛·瑟嫚实在是扮演了一个李小龙式的女性复仇者。《精武门》中的李小龙,被家仇国恨逼迫得几乎丧失人性,影片中有一个段落演他在墓地藏身,表情狰狞,过度强烈的情感使他“走火入魔”,完全变成了复仇机器,而他最终因为疯狂的复仇陷入绝境。相比之下,《杀死比尔》中的乌玛·瑟嫚在当代视觉特技的帮助下,但更主要的是在与中国近代史绝然不同的背景中,以华丽的动作完成了无以伦比的复仇表演。《杀死比尔》在电影风格上体现了塔伦天奴的后现代狂欢,但却也正因此而背叛了中国功夫片的悲壮美学。
霍元甲——李小龙的“功夫神话”,是“国人渐已醒”的历史情境中的宏伟戏剧,而这场戏剧之所以打动人心,是因为它离不了悲剧的结局。让我们再一起重温《精武门》的最后一个镜头:李小龙走出精武门,迎着托枪相向的一排租界警察,纵身一跃,从容赴死。这个特意设计的最后“亮相”意在把舍身忘我的功夫精神发挥到淋漓尽致。但令我难忘的是,在这一刻里,李小龙的表情是伤心欲绝的。功夫终究敌不过枪子。
一
记得80年代初刚一播出香港电视连续剧《霍元甲》时,大街上立即就有无数青少年哑着嗓子用令人费解的粤语发音哼唱:“昏睡百年,国人渐已醒……”在人们心目中,霍元甲一夜之间成了民族英雄,功夫也几乎被目为强国之所必需。后来我念中文系研究生,在故纸堆里翻看《新青年》杂志,发现其第一卷第五期中赫然刊登着以太史公笔法写就的《大力士霍元甲传》,描述霍元甲挑战俄国和英国大力士们,志在一雪“东亚病夫”之耻。这才知道,霍元甲的传奇以及功夫的神话性,原来几十年前就已在新文化运动中埋下了伏笔。
霍元甲在上海创办精武学校,想要用武术来救国。他后来死于1910年,据说是日本人下的毒,随之有关霍元甲的叙述——从《新青年》上的文章一直到去年李连杰主演的功夫巨片《霍元甲》——始终不脱民族主义的政治色彩,遂将他的死与民族的遭遇、他的武功与中国的复兴紧紧联系起来。
事实上,多灾多难的中国在鸦片战争之后一直是“神话”高度发达的时空场域,而功夫是种种令人神往的“神话”中最流行的品种之一。在此需要解释的是,我称功夫为“神话”,不是想要抹煞功夫的现实性,我打心底里还是很佩服那些身怀绝技的武林高手的,同时也知道真功夫正不知要花多少“功夫”来磨练。我所说的“神话”,套用法国哲学家罗兰·巴特的概念,指的是我们关于功夫的话语表述方式。所谓“功夫神话”是以功夫为核心意象的一套使我们倾向于将幻觉当作真实的话语系统,它出现在许多的文学和影视作品、文化和思想议论之中,启发着我们发挥无尽的想象力,去扩张功夫在强身健体、磨炼意志、塑造新民、驱除外敌、救国救民、扬我国威等功能方面的重大意义。
这种想象模式被无数次地重写,塑造出有关功夫的一系列特定表述规范以及语境——比如提起功夫电影,我们不免立即就想到这样一些经典镜头或形象:李小龙在《精武门》飞起一脚踢破上海租界公园门口写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告示;李连杰在《黄飞鸿》中以一身漂亮拳脚打败英美侵略者;而成龙在90年代以来的一系列海外华人题材影片中(从《红番区》到《龙旋风》)不断重塑着同一个类型化的人物形象——那个其貌不扬、受人欺负(或者轻视)的中国人其实是个功夫高手,他总能临危不惧、化险为夷,取得最终的胜利。
这些令人看了感到血脉贲张的经典时刻,都说明了功夫作为某种想象或实有的“国粹”,在有关现代中国的叙述中,承担着使国人从精神到肉体都摆脱绝境的作用。但走笔至此,我的脑海里突然逼入一个似乎有些不妥当的念头——这种种影视形象中的“功夫”,或许都背负着庚子年那些义和拳高手们的尸身,最终的决斗总得是一场与外国人(或者代表外来精神的人物)殊死较量的惨烈表演。虽然义和拳运动的惨烈收场,让大家都知道了功夫敌不过枪子,但民国之后有关这场事件的记忆和叙述,很大程度上参与塑造出了一种“无所畏惧、前赴后继”乃至于“精神胜利”的伦理想象。
二
我倾向于把“功夫片”与“武侠片”区分为两种不同的类型片。“武侠片”有更古老、稳定的传统可以依托,来自中国古代文学想象的侠义精神是它的灵魂,而60年代之后在胡金铨、张彻等港台武侠片大师的作品中,形成了这种电影类型特定的美学形式、道德内蕴和政治想象:基本上采用古装,善用充满寓意的景物,以善恶正邪之争为主要情节推动力,最上乘的武功只是为了发展内力、健全人格,以内心和平为最高境界,并凭此来以一己之力对抗一个腐败堕落的世界。
相比之下,李小龙开创的“功夫片”类型,就很少有胡金铨武侠片的从容洒脱,它的语境中往往离不开民族的屈辱。功夫片的核心形象是霍元甲、黄飞鸿这一系列以功夫来战胜外族入侵者的近代传奇人物,凌驾于一切情节之上的是功夫的无比威力,而在外来强权的巨大压力之下,功夫升华为中华文化的精粹,民族复兴的指望。在这个意义上,李小龙开创的功夫片虽然极尽娱乐之能事,却也常能算得上是“感时忧国”之作。
我心目中最经典的功夫片依然是李小龙的《精武门》。这部电影的巨大成功对功夫片在70年代的复兴起了关键作用,而且也正是这部电影使“功夫”进入英语,在西方变得家喻户晓。影片讲述霍元甲死后,李小龙扮演的陈真为师父报仇雪恨,轮番大战日本武士。
虽然我没做过对于“功夫”的词源学考证,但可以相信的是,随着英语KungFu这个词汇在70年代初期流行起来,反过来也促成了“功夫”在中文中的固定意义——那些总是能找回到李小龙那里去的特定意义。但只要稍加考察,我们就会发现,李小龙的功夫片不仅在题材上把中国放置在国际背景之中,而且在其范畴层面上也是有着混血性的。只是功夫的混血性,往往在神话的浓妆重彩中被掩藏起来,而作为神话的功夫当然总是意欲强调它作为国粹的纯洁性。
在课堂上讲《精武门》时,我总会让学生们大吃一惊的地方,是我告诉他们李小龙的功夫其实不是“正宗”中国产品,而是杂糅了包括西洋拳击、恰恰舞步在内的许多异域元素。作为中国“功夫神话”最核心内容之一的李小龙的功夫,是他在海外生活的结果,这样说不仅是在吸收外来技巧的意义上,而且还与李小龙在异域的身份认同有关。出生于旧金山唐人街的李小龙,在个人经验中重新体验到创造功夫神话的必要性,而他以半个世纪之前中国的惨烈遭遇印证了自己面对强大的西方文化压力、艰辛塑造自我的历程。另一方面,从历史的角度来说,功夫片在作为殖民地的香港发生、发达的过程,也恰恰体现出了与近代中国充满挫折的“国际经验”异常相似的语境意义。
功夫片再度兴起,凭借着混血的技术、国际化的背景在香港和海外取得辉煌的成绩,或许正表现了“功夫神话”作为“想象中国”的方法之一所具有的独特政治和文化位置。而《精武门》把现代中国的“功夫神话”带到了国外,也为东方主义式的中国表述确立了一个新的指示符号。甚至李小龙也几乎成了中国人的代名词——我曾记得有一年在纽约时代广场曾遇到一个黑人对着我拼命狂吼:Bruce Lee!
与此同时,《精武门》的影像记忆在好莱坞电影中一直挥之不去,直到前几年昆汀·塔伦天奴拍摄那部异常血腥的《杀死比尔》,其中不难发现乌玛·瑟嫚实在是扮演了一个李小龙式的女性复仇者。《精武门》中的李小龙,被家仇国恨逼迫得几乎丧失人性,影片中有一个段落演他在墓地藏身,表情狰狞,过度强烈的情感使他“走火入魔”,完全变成了复仇机器,而他最终因为疯狂的复仇陷入绝境。相比之下,《杀死比尔》中的乌玛·瑟嫚在当代视觉特技的帮助下,但更主要的是在与中国近代史绝然不同的背景中,以华丽的动作完成了无以伦比的复仇表演。《杀死比尔》在电影风格上体现了塔伦天奴的后现代狂欢,但却也正因此而背叛了中国功夫片的悲壮美学。
霍元甲——李小龙的“功夫神话”,是“国人渐已醒”的历史情境中的宏伟戏剧,而这场戏剧之所以打动人心,是因为它离不了悲剧的结局。让我们再一起重温《精武门》的最后一个镜头:李小龙走出精武门,迎着托枪相向的一排租界警察,纵身一跃,从容赴死。这个特意设计的最后“亮相”意在把舍身忘我的功夫精神发挥到淋漓尽致。但令我难忘的是,在这一刻里,李小龙的表情是伤心欲绝的。功夫终究敌不过枪子。
展开全文
APP阅读